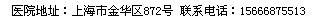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洁癖 > 洁癖危害 > 在沉默中继续歌唱与刘东明聊聊新专辑
在沉默中继续歌唱与刘东明聊聊新专辑
白癜风知名专家 https://m-mip.39.net/disease/mipso_5951583.html
文
李南心
收到刘东明的新专辑,我打开,从第一首开始播放,一直听到第六首《沉默相伴》。感觉猝不及防,心口受了一记闷锤,疼痛从神经末梢传递到大脑需要时间,这段距离在歌声中被延长,像电影里的人,中枪后会有一个慢镜头,无数画面旋转而恍惚。这首歌听上去甚至宁静优美,他唱的是:
穿过骤然倒塌的门/穿过村口干枯的河/穿过故乡夜空的黑/却绕不开人们的眼/他直起腰望一望/地头上有股热风袭来/镰刀上的血已风干/仇恨埋进干瘪的身板
我听懂了。一个再熟悉不过的故事,甚至不必去问,唱的是谁,是什么事,或是什么耸人听闻的头条。这痛苦早已渗入土地,化入江河,在每一颗种子里发芽。只要真的凝视过这片土地,就无法不感受到它。而后半段,则是这场无名悲剧的终结:
昨天他还是个壮年/盖下房子种下了田/过完今天将和他一起/魂飞魄散/你以为天下乱做一团/到头来只能与沉默相伴/河流无声夜空无星/唯有两眼望穿
听这首歌时,网上最热门的新闻是宋小女,一个等待了前夫二十六年的女人,一个被冤狱轻易翻覆的家庭,一个人青春入狱白头归来。很多人被她的访谈感动,我听到“河流无声夜空无星,唯有两眼望穿”,想到她,以及许多被遗忘了名字、消失在新闻里的人,感觉那股钝痛终于抵达了大脑,在无边的联想中扩散开。
年,我第一次听到刘东明,他在年出了一张在疆进酒演出的现场专辑《北京的雨季》,收录了他早期最好的一批歌,几乎每一首都有明快动人的旋律,朗朗上口。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他的音乐风格比较粗朴自然,融合了民间小调、曲艺弹唱的诙谐,内容多是表现底层劳动者的苦中作乐。那时他有一股明亮金黄的底色,像被太阳晒了一天的麦子,有自然、泥土的加持。我很喜欢的一首《瘌瘌秧》,描写酣畅的农忙生活,和一个憨笑自嘲的农人:
五月的天啊麦子金黄了/关中赶场的麦客你落谁家/抹把汗水你说道/挣钱不挣钱/混个肚子圆我逛世界哩/他也学着老爹的模样/旱烟抽了三锅半/昨天他还想着心爱爱呦/今天却已过了四十三
有些歌听起来已经是上世纪古老的回忆,比如描写北方平房冬天生活的《莫贪财》:早晨起来我生上蜂窝煤/铺上印有牡丹花的床单/我骑上自行车退掉啤酒瓶/去裁缝店修我的拉链/一天又一天都在这样过/什么时候学别人有房有车——仿佛能看到冬季哈出的白气,那些早已消失的生活细节,蜂窝煤、退啤酒瓶、裁缝店,在十多年后听来仍是贴肤的亲切。
也有人物特写,白描的手法,《老裁缝》,写一个慢慢衰老的女裁缝,身穿一件褪色的蓝色上衣,被时代遗忘:在一个干冷的冬天/这个老迈的女人/她步履蹒跚/慢慢缩进裁缝铺的门与窗。在当年第一次听的时候,想到有人曾经这样无声地凝视过她的背影,并且会为她写一首歌,就会觉得心头一热。觉得这样的歌者,真是对人间有种深情。
年的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把最佳男新人颁给了刘东明。那时候他已经很不新了。我看了颁奖视频,他穿着日常的T恤沙滩裤上台,说自己唱了这么多年才拿到了新人奖,希望下一个新人不要等那么久。他看上去跟这个漂亮的舞台太无缘了,像一个走错片场的盒饭演员,然后略带别扭地唱了一首《芒种》——描写农人在田间劳作的歌。
那时他刚刚发行第一张完整的录音室专辑《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听起来和过去已有些变化。单枪匹马时代直抒胸臆的感觉在隐去。《西北偏北》是他早期最广为人知的歌,称得上是一首杰作,由小引的诗歌而来。在前一张专辑里的现场版本,还是一人一琴,在暗黑中喝下一口劣质的白酒,凭着一腔血气对着狂风吟唱的感觉,苦涩耐磨。到《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录音室版本,有了更精良的编配,那种土地黄沙的摩擦感反而大幅度降低了。让人感觉到他在摸索着某种变化。
《芒种》是好作品,听上去有乡间小雨的玲珑,仍有“面朝黄土、汗洒田间”的真诚,但已经远离了《癞癞秧》时期与土地生活紧紧贴合的感觉,取而代之的是带一点“隔”的怅惘,有距离地观看,歌者自身已经不在此情境中了。
而专辑中与主题同名的歌,则比上述两者更具有真实的在场感,也让我重新感受到听《老裁缝》时那种温情脉脉的凝视。《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刘东明写某段在娱乐夜总会卖唱的生涯,那里有很多风尘女子:晚风瑟瑟每当你独自走过她身旁/她会与你搭讪先生你做不做。而他这样卑微、小心翼翼地去描述、去歌唱对她们的共情:我拿着刚买的烧饼/你要不要也来一口/这有多么的可笑/我这个没用的人
随着生活变化,上世纪的烟火以及农耕主题,从刘东明的创作中渐渐隐退,继而进入了一种被认为风格杂乱的创作期,既不是全然的城市,也不再有真的乡土。他在后几张专辑里有一些歌,很能体现在变化中呈现出的、他独特的性灵。英国科幻作家尼尔·盖曼写过一篇日本神怪主题的短篇小说《捕梦》,中文译者马骁。故事犹如幽境,曲曲折折中引人入幻。马骁的文笔也极好,行文古典而清洁,很符合原作的日本背景。这篇小说像梦境中的一朵莲花,是唯美的。但我读到它,则是因为刘东明为它写了一首歌《狐灵与和尚》。听过之后,再读小说,沉浸其中再回头来听歌,循环地掉在梦境中,令人迷醉。原作的氛围,阴郁天空下心事如尘、命运如蚁,和尚与狐女心系彼此又克己复礼,直至为彼此赴死,无怨无悔的平淡,在歌里,被他分毫不差地唱出。
而《再送陈章甫》、《天水》这样的歌,是上世纪台湾民歌的遗韵(刘东明在演出时还翻唱过李建复的《归》),散文诗一样的歌。从这里已经看不出那个嘶吼着“什么麦加什么姐妹”的刀客的影子了。
如果音乐有人格的话,在过往的创作里,他有非常市井、无赖、戏谑而故作粗俗的一面,是充满烟火气的脏与活力,是可爱的;另一面则严肃、幽静、深情、有文人气。前者属于土地与童年,后者是漂流于城市中的、不愿多言而只愿从音乐中道出的净土,是洁癖。
老裁缝被时代淘汰,农人跌倒于城市化的拆迁中,大量的人离开土地,也不能在城市中安居。过去十多年里,民谣从田野、根源转移向城市。但在转型的夹缝中,真正脱胎换骨又是何其不易。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听刘东明的时候,会想着,他还会再唱那些“面朝黄土”的人吗?或者,还会凝视那些寒风中的背影吗?
到今年的这张专辑,恰好是得到最佳新人奖的十年后,听到《沉默相伴》,我知道他会的,会一直这样唱下去。
而此时此刻,重新打开《北京的雨季》,再听《癞癞秧》,我感到很悲伤。这是属于我自己的一种联想,对这个小人物在时代长河中的命运的一种猜测。一个农人,曾经是这样乐观地躺在大地之上,只求混个肚子圆好逛世界,转眼就到了中年——穿越到未来的另一首歌里,他已然衰老,昨天他还是个壮年,借钱、盖房子、多种点粮食,今天,他在无法预料的一场人祸中骤然倒塌,走向扑面而来的夜色如水深沉。他的灵魂飘浮起来,向下凝望焦黑的故土,与人世的悲剧告别。我心碎了。多少人事物,在时代大浪中逐一破灭,除了音乐,我们确实只能与沉默相伴。也幸好,还有人在沉默中继续歌唱。
访谈者
李南心、陈郁(摇滚乐杂志撰稿人)
南心:二哥,你好,先祝贺你的新专辑即将发布。我先听为快,很欣喜,感觉有一些阶段性的变化在里面,一方面是曲风,另一方面是人的状态。在以前的专辑里你说过,因为被批评曲风太杂,你就索性做得杂一点。但这张新专辑整体听起来很协调,这是有意识的变化吗?
刘2:你好,小南。是的,我和波波(邢江波,新专辑编曲/录音/混音/制作人)在专辑前期准备时就达成共识,就是这张我们都想做得更简洁一些。因为从《大地迷藏》那张开始,我俩想融入一些民谣以外的音乐元素,延续到《新编好了歌》也是,不过后来再去听,会发现并不理想。举个例子,像《再送陈章甫》,刚开始做出来我们都很兴奋,现在再去听就觉得很失败,不好。所以这张我就想让它更“民谣”一些。申明一点,之前我说因为别人批评我才做得更杂,那是玩笑,我们编曲时基本不会考虑别人的话。
陈郁:二哥现在有了丈夫和父亲的身份,心理上变化大吗?
刘2:心理这个东西说不太好,绝大多数时候我觉得没什么变化,我很少主动把自己放在一个丈夫或父亲的角色里面去,那样会不太自在。总感觉自己还没长大,不愿意去面对更多事情。但有时候也会不一样,比如我偶尔也会去幼儿园接女儿放学,就会想到别人的家庭,会想一个常规家庭里的父亲对于子女的给予。就是那个传统里所说的“责任”,在我这里,还需要慢慢地去调整。
南心:这是我想说的第二个变化,这张专辑让我第一次听到你有了中年的平静与温暖。像《红菜汤》,反反复复地唱那一句,有一种无奈的温情。作为十多年的听众,这种变化让我很触动。家庭生活对创作影响大吗?
刘2:对,你说得没错,是一种无奈的情感。但它不一定局限于家庭,也可能是朋友间的友谊或者其他什么人。这首歌的开头段落来自朋友邱小孩的一首歌的副歌部分,我把它放在了前面。我理解的他那首歌,就是一个人对于生活的无奈,不管过得好坏,就算到了世界尽头,不过想住一间不漏雨的房子,吃一口热汤饭。那么好吧,我愿意为你熬一锅红菜汤,在你饥寒交迫的时候。
陈郁:你写《沉默相伴》和《滚动的脸盆》这样的歌,是因为这都是真实发生过的社会事件,这两首歌让我获得了一种安慰,就是还能感觉到“我们”的存在,而不是“独善其身”的虚无。但大环境我们也都清楚是怎样的现实,社会关怀一类的歌词往往要变得曲折,或许听到这些歌的人还会考量一下别人的惨痛经历在歌中是否产生重量而不会变得轻佻。你决定写这些歌时,会考虑这些吗?或者说是什么直接促使你写出这些歌?
刘2:人活着是要有良知的,否则和动物没区别。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我生活的时代,有的就在我身边。年冬天北京大批清理外来务工人员,波波的母亲就是其中被清理的对象,必须离开。你在自己的国家,在生活多年的城市,被强行驱逐出去,这算什么?我后来问过波波,他母亲现在浙江一个城市打工。我唱出来,其实和你吃完晚饭和别人闲聊天一样,可能没有一点作用,但不能麻木,不能视而不见。
南心:大概从周云蓬的《中国孩子》之后,有一个概念经常被提起,“抗议民谣”,好像民谣应该肩负大于其他音乐类型的道义感。你觉得民谣跟时代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民谣有映照现实的责任吗?
刘2:我们最早知道“抗议歌曲”是来自于西方,反战、反集权等,像鲍勃迪伦、平克、U2等等都有很多经典的抗议歌曲流传下来。《中国孩子》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值得聆听的声音,那些个体的苦难不应该被遗忘,因为它们来自人为的错误。“责任”不能依附给艺术形式或者某个艺术家,那是政客才要担当的。像我上面所说,艺术家更多的是出于一种良知去创作。
陈郁:说到社会关怀,长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