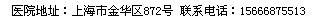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洁癖 > 治疗医院 > 张全之论鲁迅的志士之祸纪念鲁迅诞辰
张全之论鲁迅的志士之祸纪念鲁迅诞辰
▼
编辑部推出三大措施扶持青年学者
《探索与争鸣》第二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征文
活动进行中(点击蓝色标题可查看)
鲁迅专题:
1.孙郁:鲁迅不是远离我们的存在,而是一道与我们息息相关的风景
纪念鲁迅诞辰周年①
2.吴俊:鲁迅必须活在真实中
纪念鲁迅诞辰周年②
3.赵京华:破解狭隘的民族主义壁障——作为精神资源的鲁迅后期国际主义
纪念鲁迅诞辰周年③
4.谭桂林:鲁迅如何用世界眼光讲述中国故事?
纪念鲁迅诞辰周年④
5.张文江:一个古典研究者眼中的鲁迅
纪念鲁迅诞辰周年
6.李怡:新语文如何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拿来”
纪念鲁迅诞辰周年⑥
7.高远东:鲁迅“相互主体性”意识的当代意义
纪念鲁迅诞辰周年⑦
论鲁迅的“志士之祸”
张全之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澳门大学兼职博导
本文系年4月,《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东方青年学社共同主办的“拿来主义与文化主体性:鲁迅传统中的中国与世界——纪念鲁迅诞辰周年暨逝世80周年(上)”圆桌会议上的发言修订而成,原载于《探索与争鸣》年第6期
“志士”一直是一个褒义词,指那些有高尚志向和道德节操的人。
孔子曾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从此“志士仁人”或“仁人志士”就成为汉语中极富表彰性的词汇,一直沿用至今。
但在鲁迅笔下,“志士”常常成为他讽刺、挖苦甚至贬斥的对象。在《破恶声论》中,他谈到一些所谓的“志士”禁止农人搞祭祀活动时就愤怒地写道:“农人之慰,而志士禁之,则志士之祸,烈于暴主远矣。”正是在这句话中,鲁迅提出了“志士之祸”的概念。
从《破恶声论》整篇文章来看,鲁迅对“志士”的讨伐,不只限于禁止农人娱乐这一件事,而是针对当时社会上的种种乱相,充分表达了他对“志士”的厌恶与批判。“志士”历来被看作社会的精英、民族的栋梁,何以会遭受鲁迅如此激烈的笔伐?这不能不引人深思。
要搞清楚“志士之祸”的含义,先要分析“志士”一词在《破恶声论》中的含义。纵观全文,“志士”一词一共出现了15次,分别归属在13句话中。此外还有含义十分相近的“伪士”一词,出现了一次,未列入统计数据。为了后面的论述方便,我将这13句话划分为五组,具体如下。
第一组:……志士多危心,亦相率赴欧墨,欲采掇其文化,而纳之宗邦。
第二组:(1)今者古国胜民,素为吾志士所鄙夷不屑道者,则咸入自觉之境矣。(2)崇侵略者类有机,兽性其上也,最有奴子性,中国志士何隶乎?(3)而吾志士弗念也,举世滔滔,颂美侵略,暴俄强德,向往之如慕乐园……(4)今志士奈何独不念之,谓自取其殃而加之谤……
第三组:(1)虽中国志士谓之迷,而吾则谓此乃向上之民,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者也。(2)国民既觉,学事当兴,而志士多贫穷……计惟有占祠庙以教子弟。(3)若在南方,乃更有一意于禁止赛会之志士。(4)号志士者起,乃谓乡人事此,足以丧财费时,奔走号呼,力施遏止……(5)农人之慰,而志士犯之,则志士之祸,烈于暴主远矣。
第四组:……然此破迷信之志士,则正敕定正信宗教之健仆哉。
第五组:(1)故病中国今日之扰攘者,则患志士英雄之多而患人之少。志士英雄,非不祥也,顾蒙帼面而不能白心,则神气恶浊,每感人而令之病。(2)顾志士英雄不肯也,则惟解析其言,用晓其张主之非是而已矣。
以上五组言论,除第五组是总论“志士”的特点外,其余四组分别代表了四类人,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组指面对民族忧患,率先赴欧美学习先进经验,“苏古纳新”以图救国的知识分子。鲁迅一方面肯定了他们在救国问题上的积极努力,认为“中国之人,庶赖此数硕士而不殄灭”,但同时鲁迅也指出,他们学习西方仅得其皮毛,未能改变中国的“寂漠”状况。
第二组指那些鄙视印度、波兰等落后国家,崇拜武力,崇尚侵略的进化论者和主张以武力解决中国问题的革命者。这一观点在《文化偏至论》中也有表达,他将那些“竟言武事”的人,讥为“辁才小慧之徒”。
第三组指那些反对宗教、反对迷信的文人。清朝末年,由于义和团运动大力宣扬迷信,引发了士人对迷信的反感;又加上庚子事变引发的危机,清政府被迫实行了“新政”。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破除迷信,“废庙兴学”。鲁迅对这一做法十分厌恶,愤怒地写下“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的句子,其中“伪士”是对“志士”的进一步贬称。伊藤虎丸认为,“伪士”指保皇派的改良主义者,这是不准确的。在“清末新政”中,主张并实施“废庙兴学”的大有人在,不只是康梁师徒。
第四组指提出“改儒学为孔教”的康有为等人。儒学并非宗教,但康有为有感于西方宗教的强大势力,试图将儒学宗教化来对抗耶教。他在年《康子内外篇》中,首次使用“孔教”一词,并与佛教、耶教并称。年和年,康氏两次上书朝廷,建议遍设孔庙,祭祀孔子,将儒学定为国教。康的主张受到了章太炎的激烈批评。鲁迅显然受到章氏的影响,也对康氏的主张痛加打伐。
由上述四个方面不难看出,“志士”并非专指某一类人,而是指当时活跃在中国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的各类人员。可以说,年轻的周树人满怀激情地横扫了当时中国社会上的各路救国豪杰,这一批判立场跟《文化偏至论》是十分相似的。《破恶声论》其实就是《文化偏至论》的姊妹篇,“恶声”来自于文化上的“偏至”,二者互为表里。
鲁迅极善于对复杂的现象进行简洁地分类,像纷繁复杂的中国历史,被他直接划分为“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同样,对于上述这四类人物,鲁迅在《破恶声论》中直接一劈为二为“妄行者”与“妄惑者”:“(妄惑者)狂蛊中于人心,妄行者日昌炽,进毒操刀,若惟恐宗邦之不蚤崩裂”;他所期待的“独具我见之士”,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洞瞩幽隐,评隲文明,弗与妄惑者同其是非”。
所以,“妄行者”与“妄惑者”从言论和行动两个层面,概括了他所要批评的“志士”。
对于众多的“恶声”,鲁迅也划分为两类:“一曰汝其为国民,一曰汝其为世界人。前者慑以不如是则亡中国,后者慑以不如是则畔文明。”前者概括了腾沸于人口的各种救国论调,后者指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当时主要是以刘师培为代表的“东京派”和以吴稚晖等人为代表的“巴黎派”,本文中的“志士”主要指的是前者。
作为一位年轻人,鲁迅何以对当时活跃在中国舞台上的各类“志士英雄”采取如此激进的批判态度?这主要基于他对这些“志士”的深刻观察,发现了他们身上难以克服的缺陷,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自私。早在《文化偏至论》中,他就敏感地意识到,那些主张“以习兵事为生”的革命者“虽兜牟深隐其面,威武若不可陵,而干禄之色,固灼然现于外矣”;那些主张“制造商贾立宪国会”的改良者不过是“假力图富强之名,博志士之誉;即有不幸,宗社为墟,而广有资金,大能温饱”;至于那些“识时之彦”,除了一些“盲子”之外,“少数乃为巨奸,垂微饵以冀鲸鲵”。
在《破恶声论》中鲁迅继续批判这些志士“掣维新之衣,用蔽其自私之体”,“不得不假此面具以钓名声于天下”。
这些批判,都基于“志士”们的动机:他们在冠冕堂皇的言行背后,隐藏着自私自利的诉求。在这里我们看到,鲁迅将“动机”作为评判“志士”们言行的出发点,表现了鲁迅在评价人物时不仅看你做了什么,还要看你为什么去做,这种深刻的观察,很容易洞穿那些虚伪的假面。
但另一方面,它也显示了鲁迅在救国问题上的理想主义倾向和在知人论世方面存在的道德洁癖。所以他强调“爱国出于至诚”,“诚于中而有言”方是真正的爱国。
这种道德上的洁癖,在鲁迅的一生中一直存在着:他做事力求完美,看人总是多疑,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对中国“正人君子”的批判,也是这一思路的延伸。
二是肤浅。他痛恨那些“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的“志士”们,“灵府荒秽,徒炫耀耳食以罔当时”,实则是欺世盗名之辈。在批评以科学反对迷信时,鲁迅嘲笑了那些只知道“鬼火”是磷、人体是细胞这些皮毛知识就四处卖弄的人,“虽西学之肤浅者不憭,徒作新态,用惑乱人”。正是这些人,制造了一个看上去“扰攘”实则“寂漠”的世界。
在《破恶声论》中,“寂漠”与“扰攘”是一对相反的概念,中国当时一方面“言议波涌,为作日多”,“靡然合起,万喙同鸣”,但由于这些声音“不揆人心”,都是表面文章,所以越是热闹,越显得寂寞。在晚清众声喧嚷、各种思潮腾涌的喧闹声中,鲁迅应该是唯一一个感到寂寞的人,这种寂寞表明了他与当时社会思潮之间的巨大分歧,说明他已经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思想路径。
三是聚众。晚清的义和团事件和庚子事变,导致了封建王朝的严重危机。朝廷开始实行“清末新政”,试图延续自己垂危的命脉,同时各路英豪也各显神通,从西方拿来了各种主义和方法,“有科学,有适用之事,有进化,有文明”。
具体来说,当时鲁迅身处的日本,是中国政治家和各种政论家的舞台,改良与革命、世界大同与暗杀,“金石黑铁”与“新民”,各种论调纷纷亮相,各自吸引了一批追随者。
在鲁迅看来,这些聚众喧哗的各种论调,“寻其立意,虽都无条贯主的,而皆灭人之自我”。鲁迅似乎是天生的少数派,看到聚众扰攘的场面,就心生疑窦。在《文化偏至论》中就提出了“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主张,到《破恶声论》,这一主张得到了更大的发挥。
四是无信。鲁迅在《破恶声论》中表达了对信仰的态度:有信仰强于没信仰,哪怕信仰的是鬼神之类的原始宗教;但无信仰强于被迫信仰某种外在的宗教(或理论),所以他对康有为等人的儒学宗教化,给予了批评。中国虽然不是一个有严格宗教信仰的国家,但民间自有自己的信仰对象,这就是被“志士”称为“迷信”的东西。
面对着以科学反对迷信的运动,鲁迅起来为迷信辩护,这是否意味着鲁迅站在迷信的立场上,反对科学?事实并非如此,这需要从三个方面去理解。
首先,鲁迅认为宗教是人类精神生活必须有的依托,他认为“人心必有所凭依,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
其次,中国的原始信仰,保留了人性中极为纯洁的部分。中国虽然没有西方那样的一神教,但中国人“普崇万物为文化本根”,是极为宝贵的精神传统,正是这一传统保留了“气禀未失之农人”,与之相比,中国的士大夫由于丧失了这种原始信仰,导致人性的堕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出了“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的话。
再次,鲁迅认为科学与宗教并不矛盾,都是人类精神所依靠的宝贵财富。西方早就有将科学与宗教合二为一的传统;尼采虽然借达尔文的进化学说批判耶教,但他从没有否定信仰。所以科学与信仰并不相悖。至于中国那些借助对科学的一知半解就废庙兴学,或以反对迷信之名,禁止农人祭祀神灵的行为,都是粗暴的,这就是鲁迅所谓的“志士之祸”的最直接的含义。
以上四点,其核心就是虚假、虚伪与虚饰。在鲁迅看来,无论是来自西方的种种理论,还是从古代发掘出来的种种救国学说,都不是从提倡者的“渊深之心”发出来的,都是“不撄人心”的外在理论,与人的内心无关,自然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由此看出,鲁迅这时期的启蒙主张,不是借助西方的种种理论,来破除中国的愚昧和麻木,而是通过反诸内心的方式,唤醒“真的人”,他说“患志士英雄之多而患人之少”,就将“志士”和“人”对立起来,所谓“人”,就是拥有“心声”和“内曜”的独立个体:“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
这种寻找诚与真的努力,是鲁迅启蒙思想的一大特色,也是他在日本时期思考中国问题的基本思路。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时候,就说中国文化最缺乏的是诚与爱。
可见,他将“诚”看作是破人荒的途径,为此他提出了“白心”的概念:“志士英雄,非不祥也,顾蒙帼面而不能白心,则神气恶浊,每感人而令之病。”“白心”一词出自《庄子·天下》篇,原文为:“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苛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白心”即是表白心愿,或指赤子之心,都是在呼唤着“志士”的真诚。
但在当时的中国,这样的“至诚”之音茫不可见,他只能从西方去寻找知音:“奥古斯丁也,托尔斯泰也,约翰卢梭也,伟哉其自忏之书,心声之洋溢者也。”在鲁迅看来,只有如此真诚的“心声”才是拯救中国的不二法门。
鲁迅对“白心”的期待,对“心声”的呼唤,在晚清时代,可谓空谷足音,没有应者,也在情理之中。今天看来,在一个民族面临危亡的时候,提出这种极端理想化的主张,显示了青年鲁迅心中的浪漫情怀和过高的自我期许。
毕竟救国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一部《忏悔录》到底能起多大作用,是值得怀疑的。在动机与手段之间,过分看重动机的纯洁性,也值得商榷。
鲁迅在道德上的洁癖,注定了他孤独的命运,“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了自己:就是我绝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看来他曾经误以为自己是这样一个英雄。正是这种“英雄”心态,使他走向了一条个人的孤绝之路。
回顾鲁迅撰写早期这些文章时的历史,很多遭到鲁迅批评的“志士英雄”留在了历史上,而鲁迅发出的这些愤激之言在当时根本无人问津,沉睡在故纸堆里。所以过分高估这些言论在当时的意义,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鲁迅当时这些思想,与那个时代并不合拍。但今天,当我们重新阅读这些文献,重新思考鲁迅当年思考的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不震惊于他思想的穿透力,他这些掷地有声的文字,像电光石火一般激荡着我们的心灵。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更加扰攘的世界,利益的追逐、肤浅的喧嚣、聚众的战术依然环绕在我们周围,“志士”们的高谈阔论依然横行,而“心声”“内曜”仍不可见,“正信”不清,信仰倾覆,“至诚”不见,“白心”匮乏仍是当今社会的重要问题。
在这样一个扰攘嘈杂的世界里,重读鲁迅这些文字,不能不让人感动、感慨而又颇觉无奈。
有事找小探(suo,记得备注姓名和单位哦)
END
人文社科学者的平台
《探索与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