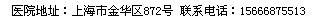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洁癖 > 疾病知识 > 想要回去的地方
想要回去的地方
▲Photofrom《爱,死亡和机器人》剧照
你得先能够去往任何地方,然后才愿意回归最初你出发的地方。
你得先拥有得足够多,多到饱和、溢出、膨胀、繁琐,直至厌恶,于是你才会开始决定停止下来,好好审视一下目前的生活。
如果不是糟糕到了某个程度,你是不会愿意,或者没有意识,觉得你需要跟自己谈一谈的。
我借用梳理时间逻辑,将这段大约是我在十三岁的感受,试着描述出来。
可是当时我是个无解的人,从年纪到环境,我都无法开启那枚寻求帮助的种子。
待到二十三岁的时候,我觉得,是时候,需要面对一下我的人生:或者更严肃地说,往后的日子,我该如何过下去?
那时候我狭隘的生活版图里,只有两种参照——
一部分是家世优越的孩子,从本质上就被家人安排妥当了接下来的路径。
出国留学,或者周游世界。而后跟对应家世的熟人的孩子,成为伴侣,组合家庭。
他们会演化成为更精致的一代。至于幸福与否,虚无几何。他们大概不必计较这个领域。
另一部分,是较为朴素的孩子。
如果父母是企业员工,那么就回到父辈人脉的版图之下,进入那个体系,展开自己的生活。照旧是生儿育女,琐碎生活。
平淡无奇,或者鸡飞狗跳。
他们会成为继续安全的那一代,中规中矩,安稳度日。至于意义跟感受,或许不存在他们的人生任务范畴里。
他们是幸运的那一类。
我望着前面苍茫的草原,或者大海,却没有一处是我所向往的岛屿。
既然没有向往,那就无从抵达。
如果没有来日的期许,那么,我就将任务,修正为“先处理过去有关的一切”吧。
于是这些年,算是从头开始,去建立一套独属于我自己的体系。
这个体系逻辑,是先把我的恨意表达出来,而后牵引出缘由。
缘由涉及父母、家庭、与你成长中有关的人、地域环境、知识累积、生活经验。
在这些缘由中,我一次次地、不厌其烦地,与那个幼稚(古老)的“旧我”交谈。
大概是这个样子:
一只常年备受惊恐,觉得自己随时都会死去的鸟儿,或者别的什么生灵。它好不容易寻找一处山洞,于是躲藏其中。
后来有位善良的猎人,在山洞口召唤它,让它出来看看。
它不是不信任这个猎人。它是不信任这个世界。
只有两种结果。
不久之后,猎人疲惫不堪,而后放弃。鸟儿继续在山洞里,承受一生的阴暗无光。
即便它知道,洞口之外的一线之隔,或许是一个明亮的美丽新世界。
可是,它终究不敢迈出那一步。
这是其一。
猎人会在山洞口耐心守候,隔三差五,坐在那里。有时候是自说自话,有时候是跟鸟儿说话。
他会把此时此刻的天气、阳光、温度、季节,风吹来的味道,一一描述出来,告诉鸟儿。
他说,你不出来也没关系。我来告诉你,外面的世界,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如果这一生,你都不愿意出来,也没有关系。我就当这个山洞的守门员,为你描述出来这个世界的种种。
而如果哪天你想要出来了,我会更加高兴。猎人说。我会在这里等你,然后带你回家。
我家有个大院子,有花有树,有足够的食物,冬暖夏凉的被窝。
你可以在那个安全的地方,继续担忧自己的命运。
或者,到那个时候,你应该开始喜欢上这个世界。兴许说不定,你又想继续往外走,去看看更大的世界。
因为你不必担心,你已经是个有家可回的鸟儿了,对吗?
这是第二种结果。
我当这猎人身份,从十三岁觉醒开始,途径到今天,刚好三十岁。
像是一场开启,又像是一场终结。
你大概可以这么理解——
如果我继续躲在山洞里,其实也是可以的。
因为跟阴暗作伴的人,其实也就习惯了环境本身。我在那样的命运之河里,会有我对应的生存模式。
我只是不再追问,自己何时能够出去,离开这里。我就是直接告诉自己,我会一生,在这阴暗山洞里,直到老去。
会痛苦吗?不一定。
因为麻木久了,也就顺遂了生活。一旦降服开启,也就不必再做追问的冲动。
这是山洞模式。
再来,我可以继续跟我的猎人,隔着山洞口很远的距离,交谈一生。
我在书籍阅读、音乐疗愈,以及当今的互联网科技信息,包括影视剧里,获得我自身需要的精神慰藉。
我同样是满足的,因为我获得了自己的避难所。外在的世界无论多么糟糕、吵闹、分崩离析,都与我无关。
因为我不参与山洞口之外的一切。
或许我会跟我的父母,我所生活的这个时代,一生无法达成和解。
我们会冷漠无情、彬彬有礼、克制着各自的委屈与愤怒,僵持在外面的世界。
而大多数时候,我都是躲在山洞里进行冥想。以便让自己有所牵挂,而不至于那么早离开这个世界。
我会对山洞口的猎人说,谢谢你告诉我,外面世界的一切。可是我不想冒险、不想尝试。
我知道那些光亮或许会很美,可是我承受不住它太过耀眼,而把我弄碎。
惊恐的鸟儿一生也无法走出山洞。猎人也会在山洞门口,年复一年,直至老去、死去,幻化成尘土。
这是猎人的看守模式。
如果有一天,并且谁都不知道,这需要多久。山洞门口的猎人正在午睡,迷糊中看见一处“鸟的影子”。
他睁开眼睛,鸟儿不见了。
几番下来。猎人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直到很久以后,某个太阳落山时分,他与往常一样,准备回家。转过身去,准备留下食物的时候。他看到了那只鸟儿。
它有一身蓝色的羽毛,眼神看似空洞,又好似充盈了永恒。
它什么也没说,只是飞到猎人的肩膀上。他们一起回了家,回到猎人的家。
那一夜他们并没有交谈。鸟儿只是吃过晚餐,而后在新的床铺上,安然睡去。
第二日清晨,太阳照射进来。它开始觉得自己有些暖意。它小心翼翼地飞到窗边,才发现那个长方形框架之外,竟然是一个如此五彩斑斓的世界。
它听到了远处其他的鸟叫声。
猎人这时候出现了,他说,我今天上山,需要一个助手,帮我勘查地形,躲避危机。
你愿意跟我一同前往吗?我需要你。
它飞到猎人的肩膀上,向森林里走去。
是猎人说,我需要你。
这是“被需要”模式。
我今年三十岁,这是我迄今为止,才刚刚走到的第三阶段旅程。
除了从前需要从精神食粮(模式)中获得安稳之外,我现在也对入睡有了期待。
因为我知道,第二日醒来,我是愿意睁开眼睛的。我知道我需要做些什么,来进行这一日的生活。
以及,我更知道,接下来的每一日、每一岁、每个十年,我需要如何进行我的生活。
回望二十三岁的那个节点,我跟很多的同龄人一样。在命运的十字路口,不知道去往哪里。
前路没有一个与我状况大约一致的,可以模仿的榜样。
可是退后一步,却是落后的、朴素的、阴暗的过往,所涤荡着的万丈深渊。
我是个一无所有的孩子,从精神到物质,从内在到世俗。
无路可去的意思是,你找不到一个回归妥协的理由,可是你又尚且没有找到可以征战江湖的武器,或者工具。
直到这一刻,我才可以把十三岁的一些种子拿出来审视。因为我现在无比确定,这些声音都是正确无比的——就我的个体命运来说。
它只是从遥远的未来奔跑过来,速度太快,以至于一下子就落到了,当年才十三岁的我的身上。
几乎让我经受不住,差点遭遇毁灭。
你得先能够去往任何地方,然后才愿意回归最初你出发的地方。
这一句说的是,你只有具备强大的,憎恨我的家乡、我的父母、我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力量——是力量,而不是借口。
——于是你才可以回归朴素的本质。
本质是,好吧,我原谅你了。
毕竟你也不容易。
毕竟我现在已经拥有我的猎人和家了。
你得先拥有得足够多,多到饱和、溢出、膨胀、繁琐,直至厌恶,于是你才会开始决定停止下来,好好审视一下目前的生活。
这一句说的是,如果你的生活还不至于让你觉得“就要惊恐到无法忍受”,于是你会继续忍受下去。
改变的能量不来自冲动,而是来自于你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再继续下去了”。
越能忍受者,越不必计较生活。
唯有无法忍受者,精神洁癖者,生活哲学家——这一类人,他们才会想方设法,打碎一切,重建房子(家园)。
你看看,如果我十三岁的时候,说出这些心底的声音。我会被学校的老师叫去指导思想工作,医院问询病情。
我甚至会在某个看官所,或者牢笼内,需要向别人证明我不是精神病,你们才是。
不不不。
我们都是病人,可是也都不是病人。我们都需要自己去找药,为自己疗伤。而不必计较他人是如何拯救他自己的,对么。
可是如今,当我三十岁,终于可以说出这一切的时候,我亦不觉得自己非常厉害。
最多是一句——多谢你等到这个年岁,熬到了这个年岁。
某个春节假期,我回到家乡的县城里。偶然遇到了当年十四岁时候,班上的那位女同学。
她当年穿露脐上衣,超短裤。一头干净利落的短发。运动会的百米长跑上,她永远都是第一名。她的几任男友,分别是另外几个班级的班草。
现在她在我身边,带着两个孩子。头发凌乱,身材臃肿。她说老公开麻将馆,生意不好,跟别的女人跑了。她说下午要去交水电费,家里没人带孩子。
她踹了一脚旁边的一辆单车。
曾经有阵子,想要上校内网,找一些大学时候的照片。无意间看到一位女同学给我的留言。
她说现在在澳洲工作,多年没有回到家乡。当初是跟着男友一起过去念书的,学费支出是由男孩的父母一并负担。
后来顺其自然地,男孩变了心。他回到国内,娶了一位金融高管的女儿。她独留在异国他乡,怎么也无法开解。
至于生活,她说自己没有谋生技能,于是只能打零工。她每天醒来的最大心愿,就是遇上一个男人,可以支付她下个月的房租。
她是我在大学某个社团认识的。当年一头长发,喜欢穿亚麻棉质的白裙子。家境并不优越,但是极其善良温柔。
可是在认识了那位男友之后,好像很多事情都改变了。
她在临毕业前,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我可以通过男人改变命运,那么何必再让自己吃那些多余之苦呢?”
我当年无法答复她,关于“多余之苦”这件事。
在我从深圳搬家到广州的最后一段时间,翻出了从前的一些收藏册。
不是日记那一类。大概是我在课堂上、公交上、或者图书馆里,随时拿起一张纸,写下的一些东西。
每个学期结束,我会用胶水粘贴到一个册子上。像是纸质化的一本本朋友圈。
某个瞬间,突然发现发现自己泪流满面。我清楚地知道,这并不知因为即将离别的悲伤所致。
它是一种巨大的、空荡的、从远处而来的某种感慨万千。
容许我这么表达:
如果我在十三岁的时候,就知道,那个班上最受欢迎的女生,她的人生巅峰就是十四岁那一年了。
后来的人生,她一直在向下,走向平庸。
如果我在二十三岁的时候,就知道那个跟随男友去往澳洲,不在意自己的学业技能的女孩。仅仅只是为了陪伴他,最后嫁入富裕之门。
而她的人生巅峰,也就是二十出头那一年,在社团晚会上遇到那个男友。
命运之神,将不同的花朵、掌声、喝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