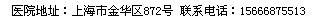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洁癖 > 疾病知识 > 卓识法治国的洁癖对话Jakobs
卓识法治国的洁癖对话Jakobs
编者按
本期小编:何天翔
自雅各布斯教授提出敌人刑法理论以来,批判的声音可以说不绝于耳。“欧洲法视界”也用了几期的空间为大家系统地介绍了这一理论,和许多学者对其的解读。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批判的声音是否正确,在于其是否真正理解了其所批判的对象之理论。只有站在充分了解对手的基础上,理论交锋的意义方能凸显。本期“欧洲法视界”,为您带来人民大学王莹副教授对“敌人刑法”的精彩解读。让我们循着雅科布斯的思维路径,重读“敌人刑法”。
〈
法治国的洁癖对话Jakobs“敌人刑法”理论
〉
文
王莹(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声明:本文原载《中外法学》年第1期。推送已获得作者及《中外法学》授权,欢迎分享,转载请联系原作者及原载刊。
1引言:作为敌人的敌人刑法?敌人刑法是德国刑法学者GuenterJakobs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概念,用以与正常和平社会下适用的市民刑法相区别。敌人刑法的基本理念是,针对那些所谓具有持久社会危险性的行为人扩张构成要件,将刑事可罚性前置,同时限制其程序权利,对其大量适用保安处分手段,以控制这些“危险源”,达到保护社会的目的。
在Jakobs看来,当今实体法上和程序法都反映出敌人刑法的发展趋势:在实体法上,敌人刑法的势头一方面表现为构成要件扩张与可罚性前置,主要是对恐怖主义犯罪、有组织犯罪、经济犯罪,甚至包括对某些性犯罪的处罚方面,针对行为人本身的危险特质将可罚性前置,在犯罪行为真正实施之前即启动刑法,以保护社会不受这些严重犯罪的侵害;{1}另一方面体现在所适用的刑罚上,主要表现为为达到有效控制行为人的目的而大量使用保安处分的手段。{2}刑罚不再是对行为人已实施的行为的回答,而是对未发生的行为的前置反应。在程序法上,刑事被告人不再如同在市民刑法中那样具有程序主体(Prozesssubjekt)的地位,作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共同起作用的一员享受法庭审判、举证等被告人权利,其权利被大大限制。例如允许在被告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其进行通讯监制(《德国刑事诉讼法》第a条);对其进行抽血化验(《德国刑事诉讼法》第81a条);使用线人侦察(《德国刑事诉讼法》第a条)等。最为明显的是《德国法院组织法引导法》(EinfuehrungsgesetzGVG)第31条的规定。该条规定面临恐怖组织制造危及他人人身、生命或者自由的危险,在必要时可以禁止在押犯人之间或他们与外界、甚至是与其律师的联系。尤其是在9.11世贸大厦袭击事件之后,涉嫌恐怖主义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的处遇每况愈下,Jakobs指出,他们的法律地位己经不再是一般的犯罪嫌疑人,堪比战争中的俘虏。{3}这一切,都被Jakobs视为是敌人刑法思想在实在法中的确证。
敌人刑法的理念发端由Jakobs在年的论文《法益侵犯前在领域之犯罪化》{4}中提出,至今一直颇受争议。批判意见主要是从法治国原则的角度出发,认为它有悖于法治国思想,甚至是对法治国思想的一大亵渎。{5}敌人刑法意欲成为与社会危险人物作斗争的刑法,没想到自己却首先沦为一个危险的刑法理念。批判者甚至将他与德国的纳粹历史相联系,指出“敌人”的概念因袭纳粹刑法学者CarlSchmidt“朋友与敌人”的范畴思路,在其中读出法西斯主义情结。{6}因而围绕敌人刑法的论战也不免连带了几分政治色彩。
但是将敌人刑法斥为一个政治上不正确的理论,对之不进行审慎的观察就径直加以抛弃,绝不是一个正确的科学态度。究竟敌人刑法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论?作为功能规范主义刑法思想的创立者,Jakobs一向致力于对德国刑法进行教义学上的精雕细凿,何以在其学术晚期突然跳出法治国刑法的成熟格局,在其之外另辟敌人刑法的蹊径?本文将循着Jakobs的思维,对由于过多转述与批判而有失真之嫌的敌人刑法理论进行文本还原,并尝试在此基础上与之展开一场智性的对话。
2敌人刑法:Jakobs的逻辑接下来我们将跟随Jakobs,循着他的思维路径,试图理解“敌人刑法”这一堪称当今德国刑法界最具有争议的理论构造。
(一)法益理论VS.规范适用理论:概念的起源
Jakobs“敌人刑法-市民刑法”的范畴构造实际上是其规范适用理论思维的延续。在上文提到的《法益侵犯前在领域之犯罪化》{7}一文中,Jakobs首次论及敌人刑法概念。他批判当时德国刑事立法漠视自由民主的危险倾向,即以规定大量抽象危险犯等形式把刑事违法性前置,以达到为法益提供周密保护的目的。而这种现象的产生,Jakobs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法益保护思想。{8}由于法益保护论者认为刑法的任务在于保护法益,{9}循着这个思路,不仅直接侵害法益的行为是犯罪行为,对法益尚未造成直接侵害而仅仅带来威胁的行为,也应该被视为具有刑事可罚性。法益概念难于界定,具有一种无所不包的巨大涵盖能力,理论上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定义为法益而晋升为刑法的保护对象。{10}因而法益思想主导下的刑法建构,很容易漫无边际,将刑事可罚性前置,造成对个人自由领域的侵犯。例如《德国刑法》第30条规定的约定犯罪与第条规定的对犯罪行为的奖励与同意行为。Jakobs批判道,在法益思想的统治下,“凡是对法益有可能产生危险的人,都可以被定义为行为人,而这种危险何时开始产生是没有界限的。行为人的私人空间即非社会性空间不存在了,他只是一个危险的来源(Gefahrenquelle),换句话说,只是一个法益的敌人(FeinddesRechtsguts)”。{11}
鉴于法益理论的这种“危险性”,Jakobs主张抛弃法益理论,采取规范适用理论。在这里他构造了部分不法(Patialunrecht)与外围规范(flankierendeNormen)的概念,以论证抽象危险犯的合理性。他将一个犯罪行为所包含的不法内容肢解为多个不法碎片(Unrechtssplitter),认为几个甚至是一个不法碎片得到实现即可以成立刑事可罚性,而不必等到所有的不法内容都得到实现(即具体的实害行为发生)时才动用刑法。{12}抽象的危险犯即是这种情况。实现部分不法的行为触动的不是主规范,而是为主规范提供适用条件的外围规范。{13}正是在批判法益理论与提倡规范适用理论的基础上,Jakobs提出了“危险来源”(Gefahrenquelle)“法益的敌人”(FeinddesRechtsguts)的理念,显露了敌人刑法理论的端倪。
对于Jakobs来说,刑法的目的不是法益保护,而是保护规范适用(Normgeltung)。从纯粹的规范角度来看,在纯粹的规范世界中,法规范的生存目的就是要得到适用,规范有着它自己的生命,它必须被遵守。{14}但是在现实世界中,规范的运作却是有条件的。
规范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一方面与法规范对象(Normadressat)也即是行为人发生关系,一方面与潜在的受害者发生关系。{15}只有当规范具有期待确定性(Erwartungssicherung),也就是说,潜在的受害者必须能够从外部感知规范是稳定的,能够切实发生作用时,规范才会得到适用。这种对规范的信任需要一定的认知上的支持(kognitiveUntermauerung),即潜在受害人必须认识到规范违反实际发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这样人们才会信任一个规范。{16}例如,当人们比较肯定地预料到深夜在停车库内很可能会遭遇抢劫,有被伤害甚至被谋杀的危险时,那么即使人们知道自己拥有生命健康与财产权,在法律上能够获得保护,如非不可,人们也将不会前往车库。{17}如果没有认知上的支持,再合理的规范在现实社会中也不过是一个没有效力的愿望而已。{18}因而对于规范来说,对于规范的信任(Normvertrauen)至关重要。一旦规范信任被破坏,社会成员就不会再遵守规范,规范就无法得到适用。正是循着这个思路,Jakobs“发现”了敌人的踪迹,即那些从根本上与法规范作对,破坏人们对法规范信任的人。
在Jakobs那里,犯罪是对规范的违反,因而犯罪仅仅存在于有序的共同体之中。“在混乱状态之中无犯罪可言,因为犯罪是对于被有效践行的秩序规范的违反。”{19}“犯罪是对正常秩序的挑衅(Irritation),是对正常秩序的可以修正的偏离(Ausrutscher)。”{20}犯罪相当于行为人对规范的否定,而刑罚的作用就是否定行为人的这种否定,通过惩罚行为人来宣称:你的否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规范继续有效,社会形态保持不变”。{21}而如果行为人不能够或者顽固地不愿意理解这种刑罚所宣称的意义,那么刑罚的这一层否定宣称的含义(Widerspruch)即无法得到施展。但是刑罚不仅仅具有含义,而且也有具体的功用,即隔离保障(Sicherung),即将犯罪行为人隔离起来,使其不致危害社会。{22}这第二种刑罚内容,也正是敌人刑法的刑罚全部功能。Jakobs主张应该把敌人刑法作为与市民刑法相对的一个概念给予足够的重视。市民刑法通过对规范违反者处以刑罚以保障规范的适用,其前提是被处罚的行为人可以被视为一个具有认识规范和按照规范命令而行为的潜在能力的人。如果行为人不具有这种能力,而是体现了某种持久违反规范的危险特质,成为社会危险的来源,那么这时候市民刑法就不再适用,取而代之应该对他适用敌人刑法。
这样,敌人刑法的概念就藉由规范理论作为基础,与Jakobs人格体与人(PersonundIndividum)的思想联系起来。要想全面地理解敌人刑法理念,我们还需对Jakobs的人与人格思想进行简要的梳理。(二)人格体与非人格体(PersonundUnperson)
在Jakobs的规范世界中,法律是作为义务与权利载体的人格体与人格体(Person)之间的关系,这里的Person,不是仅有自然状态下血肉之躯的个体(Individum),而是具有规范人格的人。{23}这种规范意义上的人格体,能够承担责任,具有规范遵守能力。人格体作为权利义务的载体,必须履行他所应履行的义务,这种义务在刑法上就是“足够地对法律忠诚”,即愿意遵守法律。{24}而人格体为何需要承担这种义务呢?Jakobs认为,这是因为遵守规范所必需的意志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当然地存在的:
谨慎守法者可能所获有限,而不愿遵守法律者却可能建国立业,富可敌国。对于个人来说,如果说他们在任何时候遵守法律规范都是对他们有利的,即以规范为导向行事是有利的,这种说法是无法成立的,由于规范的这个制度上的缺陷,法律将这种任务加之于人格体(Person),即愿意拉萨治白癜风最好的医院白癜风难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