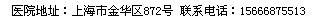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洁癖 > 疾病知识 > 幸存者的后遗症1213南京大屠
幸存者的后遗症1213南京大屠
点击上方蓝字“南京财经大学心理中心”这个周末,也许你会选择双12继续剁手,但小编更想与你一起,怀着一颗肃穆的心与祖国一起祈福和平。年2月27日,中国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将每年的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决议的通过,使得对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纪念上升为国家层面。国家公祭日的设立表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年12月13日,国家举行了首个公祭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出席,南京全城默哀。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举行公祭仪式,是要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而不是要延续仇恨。我们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为人类和平作出贡献。——国家主席习近平首设“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也成为年影响民众心理十大事件之一。幸存者的后遗症随着岁月的流逝,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人数已越来越少。目前,健在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已减至余人。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教授研究发现,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对于这些人而言,大屠杀的影响并没有随着年战争结束而消除,战争的创伤像梦魇一样一直伴随着所有经历者的一生,甚至影响他们的下一代。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某个方面来说,由于日本社会不断出现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行,学界才逐渐重视幸存者的调查。但在这种背景下,调查通常侧重于搜集日军暴行的证据,调查目的是为了反驳日本右翼的荒谬言论,而幸存者则常常是以“历史证人”的角色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事实上,现有史料足以证明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客观存在,我们应更多从人文关怀的视角,着重解决如何医治这些幸存者创伤的问题。”张连红在长期的研究中发现,除了部分自我治疗能力较强的幸存者外,许多幸存者都未能摆脱过去的阴影,年轻时的精神创伤开始“复活”,他们经常为噩梦惊醒,他们的言行开始日益偏离日常生活习惯,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精神疾病的表征越来越明显。张连红教授提到精神病学家威廉?尼德兰年提出的“幸存者综合症”,他列举了许多被纳粹迫害的集中营幸存者身上的明显症状:慢性焦虑症、惧怕再受迫害、抑郁、不断做噩梦、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快感缺乏症(不能体验快乐)、孤独症、臆想症、对世界充满敌意和不信任等。张连红在调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过程中,发现在许多幸存者身上这些症状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归纳起来,幸存者的精神创伤有三种较为典型:精神分裂型、神经质型、自我封闭型。1精神分裂型:退休工资足以度日却整天捡垃圾在张连红所调查的幸存者中,年去世的张玉英老人可谓是精神分裂型的典型案例。年12月13日,11岁的张玉英同父亲在街头被日军遇见,日军当场刺死她的父亲。张玉英后来逃到金女大难民所,金女大难民所负责人魏特琳(中文名华群,当时难民都称她为华小姐)收容她,并帮助她上学。华小姐无疑成了她的亲人。到了晚年,她日益思念华小姐,向张连红要了一张放大的华小姐的照片,挂在家中请安磕头。后来,她精神完全分裂,整天到大街上去捡垃圾,家里被垃圾塞满。张连红分析说,她的退休工资足以度日,捡垃圾的行为是大屠杀期间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经历对她的刺激所致。2神经质型:拒绝拍照“担心日本人来报复”在调查中,张连红发现有些幸存者一直处在高度警觉之中。年,他采访幸存者孟秀英老人,在她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之后,再三叮嘱千万不要给她拍照,因为她担心日本人会来报复她。张连红说,这是很典型的神经质型幸存者的案例。绝大多数幸存者在接受访问前普遍会感到心情紧张、焦躁不安,访谈时会情绪激动,访谈后很长时间不能平静,甚至连续几天睡不好觉。3自我封闭型:看到他们不承认才“忍不住说出来”自我封闭型的幸存者通常并不愿意将自己的苦难经历告诉他人,他们不愿别人去触及这一根伤痛的神经。幸存者杜秀英年出生,性格内向,很少讲话。在接受张连红采访之前,她一直没有跟任何人谈过她在12岁时遭到日军强奸的伤心往事,这次强暴事件导致她长大后三次嫁人均因不能生育而离婚。她常常做噩梦,害怕脚步声,并有洁癖。直到年因病去世,她惟一的养女也不知道养母曾经受到的伤害。在幸存者常志强的大屠杀记忆中,他的母亲被日军刺刀刺得全身鲜血,临死之前还挣扎着解开衣服为同样受伤不满周岁的弟弟喂奶,父亲跪倒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年,他在电视里看到日本人不承认南京大屠杀,“忍不住了”,主动跑到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讲述自己一家的悲惨遭遇,而在这之前,他没有向其他人包括他的子女讲述过这些无比悲伤的记忆。南京老一辈市民的创伤记忆,却已超越“原始复仇”事实上,在调查中,研究者被幸存者拒之门外的例子并不少见,也有部分幸存者通过自我修复,走出了过去的阴影。南京大屠杀这段悲惨的历史已经过去,但是,“南京大屠杀”并没有事实上也永远不可能从南京市民的记忆中消失。张连红在研究中发现,南京市民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已超越了原始复仇阶段。张连红围绕南京大屠杀对南京市民社会心理影响的问题先后做过一些问卷调查和口述访问,结果表明,在南京市民的情感记忆中,“反日情结”并不占据主导地位。而在与九死一生的幸存者接触中,张连红发现,在他们的情感记忆中,他们对待历史的态度更多的也是宽容,绝大多数幸存者的共同心愿是希望日本政府及民众能真正承认和反省这一真实的历史,防止悲剧重演。6万市民声援“谢罪的日本人”张连红举了东史郎的例子。他认为,南京市民对东史郎诉讼案的反应,是观察南京市民对南京大屠杀情感记忆的很好的个案。东史郎曾参与了年12月开始的南京大屠杀暴行。年,他整理出版了著名的《东史郎日记》,向中国人民谢罪。一些日本人认为南京大屠杀不存在,东史郎日记也是不真实的。日记中提到的日本兵桥本更就此对东史郎提出诉讼,这就是著名的东史郎诉讼案。年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东史郎败诉,年二审驳回东史郎的上诉。在一审之后、东史郎上诉期间,为支持东史郎继续上诉,南京市民在横幅上声援签名者达到6万余人。为了证实桥本残杀方式的可能,仅仅为了证明法院门口有一水塘,南京市民提供的地图就有60余件。张连红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南京市民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已经超越了“原始复仇”阶段,从某种程度上已经被置换为了一种“落后就要挨打的自责和自强意识”。“发动侵略战争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而不是日本人民,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这一观念已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在纪念馆和纪念碑的文字说明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奋发图强,振兴中华”等字句随处可见。点击“阅读原文”查看上一期“主要看气质”
赞赏
长按向我转账
受苹果公司新规定影响,iOS版的赞赏功能被关闭,可通过转账支持。
北京中科医院正规吗北京治疗白癜风什么医院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