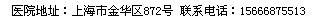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洁癖 > 预防治疗 > 庸常的意义我的
庸常的意义我的
贵阳治疗白癜风的医院 https://m-mip.39.net/baidianfeng/mipso_4624725.html
一
我坐下来。
五千年的雪啊,也一下子落了下来。
青丝随之漂白,记忆漫溯至无涯。
但当我要记录的时候,却已无话可说,唯有面对寂静的雪野,看这天地一白。
我无话可说,就像面对一部充满了堆砌和重复的鸿篇巨著,唯有歌唱:“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一样,内心当中充斥着对“惟余莽莽”之生活的歌颂。当一切的碰撞、矛盾、暗流、猜忌甚至阴谋回归于庸常的柴米油盐,安心于中华传统美德之父慈子孝鸡鸣狗叫,纵是长铗在手,亦无作歌的兴致了,还不如换几两沽酒银钱,于向晚之际,围炉夜话,与酒肉朋友聊些无关风月的家长里短。
不谈时事,才力不逮;不谈文学,无非如此。无所不谈,又无所谈。
二
人到中年正当云帆高悬之际,至于突然失语,我不认为是我个人的困境,更不是出自明哲保身的机智聪明。而是就像河水奔流到河湾时必然的的迟滞徘徊,原来摧枯拉朽的势能得到了缓冲,起初能够背负的枯木朽枝泥土垃圾,沉积起来变得逐渐难以承受。这就像一个人的负面情绪,在他注意力高度集中于奔跑的时候,他是顾不上的整理的,事不关己的情况下,甚至会对他人的抑郁予以讥讽,但是一旦沉淀下来,因为你不知道那根岌岌可危的稻草会出现在何时,反而会更加岌岌可危。
在现实中跑得越远,离心灵的回归也会越来越远。所以,有的人,干脆放弃了心灵。
三
完全从中楼把人事关系办理到现单位,是在今年的三月底。而今我人模狗样地坐在安装了中央空调的办公室里读书著文,回想起没在那座寒地孤楼之上冻死已是万幸。那时我裹棉袄而非鹤氅,戴线帽而非华阳巾,棉裤里绑着护膝,毛衣上套着护腰,袖手与窗外马鬐山相看。楼下大黄夹着尾巴狺狺而吟,守一盆残羹冷炙,几不知热馒头为何物,更不知春天在哪里。
而我去中楼之前,可谓志得意满,列了执法事业五年规划,一曰加强队伍建设,二曰引进社会治理,三曰举办论坛打造法治高地。无奈志大才疏,捉衿见肘,即便殚精竭虑,亦是两手空空,唯有敷衍塞责不堪其扰。便像孙悟空落进了老君炉,烟熏火燎之中,虽然练了一双火眼金睛,但不免见风流泪,触物伤怀;更像进了盘丝洞,一条蛛丝缚住,便会随即千万条缠身,眼睁睁居然动弹不得。遂知自己不是此道中人,仍是少年意气,终究没学会圆滑练达,又怎不会授人以柄。
吊诡的是,我上学的时候不是好学生,老是想当一个江湖豪客,甚至羡慕横行乡里的地痞流氓,但是打我步入社会方知读书好之后,胆力却越来越怯了;倒是那些原来在学校里的好学生,他们步入社会通过听话当了点小官之后,反而脾气长了胆气壮了,甚至地痞流氓起来也无师自通。读书可以使坏人变脆弱,也可以使好人变丑恶。可见读书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犹记得第一次坐公交车到中楼“赴任”,天清气爽阳光明亮,汽车在山沟沟里盘旋,竟有点异域风光的味道。正自小人得志,偏有一老妇问我:你是哪里的?说话怎么这种口音?目光中不无鄙夷。我当时应该是脸红了,觉得自己得意太早,不接地气,当好好学习。三年半后,坐公交离开中楼,山野沟壑满目萧疏,居然有仓皇不忍之意。方悟前因后果,一切都有定数。
原来那老妇早已看透了一切,当是《西游记》中观世音菩萨之化身。
中楼四年,写了一本散文集《中楼的风景》。没卖出去,没得什么奖。堆在书房里。看到它们,犹如袖手对青山。
四
今年读的书不多,写的文章犹少。
因为疫情的关系,读了加缪的《鼠疫》、詹姆斯的《人类之子》;因为从事党史史志工作的缘故,读了包括《日照县志》《安东卫志》在内的一些志书以及滨海抗日根据地的有关文献、回忆录;年底在读邓文初的《天下》,刚读完关于戊戌变法的研究资料《历史再次转向》;读苏晓《渎心者》、高军《盐道》、吴敬梓《儒林外史》以及《日照民间歌谣》后并写书评;空余时间仍旧翻翻《四书五经》,大多的时间用在了照顾家庭上了。因为调回了岚山,大女儿又考上了大学无须再陪读,于是举家搬回岚山,又租了一处房子把老家的父母接来。父母年迈多病,小女儿嗷嗷待哺,于是这一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围着锅台转,书房里都长满了草。
读书的收获还是有的,譬如《鼠疫》文本的可复制性,譬如邓文初关于地缘政治和大一统文化的启示,譬如回忆录对历史空白的填补。所谓的历史真相,谁也无法完整还原,叙述就像是万花筒中的花瓣,不同角度看过去,就有不同的图案。而如何定夺,必须了然于心,否则就会陷入迷惑。
疫情期间,写了一些随笔,事起猝然,当然亦会有激愤之言,于是按程序被有司删掉了几篇,好在本人知名度不高,否则后疫情时代亦会成为众矢之的。但这并没有完全表达我的想法,我们在反四风,反对官僚主义,但是官僚的立场并不是官场特有,而是一种群体性的癔症,越不在场,就越有控制欲望,官僚主义之所以常反常新,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群众基础”。所以这些随笔没有什么价值,只能速朽。这样算来,一年中大概也就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黄墩的风景》,另一篇是《喜马拉雅的雪豹》。《黄墩的风景》里有几处硬伤,比如描写朱信斋的凶悍,而我现在查到的武中奇回忆文章中,则说朱是一个穿长衫的白面人物,外表像是账房先生,可见人不可貌相,作文不能凭想象;另一处就是巨公山就是马鬐山一说,在《日照县志》里明白画着是两座山,因此当初采用民间文史专家的考证的确是以讹传讹。好在传播不广,亦未得奖。写《喜马拉雅的雪豹》,实在是因为出于对人的失望,还不如把注意力集中到世间万物当中去。这篇也没有得奖。
之所以强调没有得奖,不是因为淡泊名利不去凑征文热闹,而是因为自己虽然眼热但实在没有那个本领。如今省市级征文奖金俱为不菲,能得个奖贴补一下出书的亏空岂不美哉,但是实力他不允许呀。历次唯有羡慕嫉妒恨罢了。
五
回归柴米油盐酱醋茶。回到庸常的世俗生活。以至于坊间有传闻我躲在家里生孩子。可惜我没有那个功能,真是枉费诸位热心。孔子云:六十而耳顺。因此安慰一下自己,到了六十岁经历的消磨多了,才会好听的不好听的都能听进去。我还不到六十岁,虽然不必耳顺,但也不必讲个青红皂白。因为生活就是这样,哪个背后不说人?能说给你听的也未免会是你的知己。
年龄是躲不开的必然到来。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只是我往往在阅读中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人必须有另一种存在,这种存在不是时间对年龄的赋予,而是有着自己在历史当中的定位,即便你是一个庸常中人。说到历史,它是如此的苍茫和宏大,似乎我们只能做一粒随波逐流的微尘去沉浮,但是不是这样的,每个人必然有每个人存在的位置,也就是说在时间的潮流和空间的交汇之处,必然有你存在的痕迹。这种定位,不只是偶然的盲选,还带有你的主观意志,那就是: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可以天选,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则取决于你自己,取决于你对历史的认识,取决于你对自己的定位,你的坐标在哪里,你的修为就会落实在哪里。这与知识无关。
并不是号称是知识分子的人才有权对历史命名和规划,像我这样的无知分子一样可以。那就是,生而为人,不要把自己看轻。不要人云亦云,不要随波逐流,不要盲目崇拜,要做自己。
这些话可能一个自我意识初萌的初中生都能说出来,但是到了我这个年龄还这样说,自然有自己的一个思维体系。这个体系的产生,是从具体的生活中抽象出来的。是从纸尿片和刷锅水当中提纯出来的。
如此说,也可能是未到五十岁,尚不知天命的缘故吧。
在历史中定位的确是一件难事。因为历史本身并不复杂,复杂就复杂在万花筒效应上,特别是其中的影像一旦被赋予意义就不再是个人的认识问题,而会衍生出政治取向。假作真时真亦假,神剧的诞生自然有神剧的基础,那就是弱化历史真实的同时进行了主题先行,把历史给先行结论,但是历史的发生往往是偶然的小概率事件引起的,它不受理论框架的制约,而事件中人起初也并不了解事件的意义和后果,我们如今看到的某些历史,是先有结果后有事件,是对时间的结构化复述,而不是线性的自然发展。正因为正史有漏洞才会野史泛滥,正因为叙述不客观,才会有历史虚无主义。解决这个问题难也不难,不难在于每个人可以凭借图谱和传说找到自己的来龙去脉,难在于人和其族群的主观意志总是要赋予各种自相矛盾的意义。
那么问题来了:怎么证明你就是你?怎么证明自己就是自己?
所以将历史解构不是办法。每个人都应在时空当中找到自我定位,从而构筑历史。一个人的历史,是基因史,基因史即是人类史。
六
在时空中找到自己还是远远不够的。作为社会性动物,人还得找到自己的文化定位。
政治可以结果为目的,为达成目的可以妥协、苟且或者不择手段,以大多数为其指针乃至忽略个人的道德,历史则不同。真正的历史观不是政治学,真正的历史观是人类行为学。
前些日子有位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