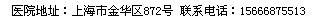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洁癖 > 预防治疗 > 孤独六讲丨革命是一种青春的仪式
孤独六讲丨革命是一种青春的仪式
点击上方绿标即可收听安静主播的领读
◆◆◆
亲爱的共读小伙伴,在昨天的共读我们看到,革命是一种激情,是青春的一种仪式;司马迁将失败者作为美学偶像,代表了他对孤独革命者的一种致敬和对权力的对抗;卓文君、秋瑾这些历史上的传奇女子,将她们的生命活出一种极致的美。
今天,我们继续领略历史上革命者的人格魅力以及革命赋予我们的思考。今天的推荐阅读章节是本书的第三章的下半部分,第页至页。
01
▼
生命最后的荒凉
我认为鲁迅是一个非常了解革命者孤独的小说家,但他自己却不走向革命。当时每个党都希望鲁迅能加入,因为他的影响力太大了。可是,从头到尾,鲁迅没有加入任何一个党。他保持高度的清醒,只是写文章感念年轻的革命者。
一九一七年俄罗斯十月革命前,帮助列宁的也多半是诗人,其中包括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他们在革命前奔走呼号,写诗让大家在酒酣耳热之际可以高声朗诵,激动人心,但是革命成功之后,两个人先相继自杀了。
有一段时间,我的书桌玻璃垫下压着叶赛宁自杀后的照片。我想大概是想警告自己,这就是革命者的下场,或者,是纪念诗人与革命者的孤独之间非常迷人的关系。
这些人的诗句多年来感动着每一个人,而他们的生命却多走向了绝对的孤独。何谓绝对的孤独?就是当他走上刑场时,他感觉到自己与天地之一切都没有关联了。
而这部分,历史不会说。
后人讲到林觉民、讲到秋瑾,称他们为烈士,所以他们慷慨赴义,死而无怨。但是历史不会写到他们也有孤独的一面,更不会提到他们生命最后的那种荒凉感。
秋瑾是在黎明之前被拖到绍兴的街口,对她而言,不但再也看不到真实的日出,也看不到整个国家民族的日出,漫漫长夜何等煎熬,这是生命最后的荒凉。
02
▼
一旦革命成功,便不可能再是诗
革命者若不是最后画下一个漂亮的句号,其实蛮难堪的。这是我一直想讲的矛盾,革命者的孤独应该有一个死去的自我,可是革命不就是为了要成功吗?为什么所有的革命者都是以失败者的角色在历史上留名?
革命者本身包含着梦想的完成,但是在现实中,一旦革命成功,梦想不能再是梦想,必须落实在制度的改革以及琐琐碎碎、大大小小的行政事务上,它便不可能再是诗。
现在我经过台北火车站、经过中正纪念馆,我想起十多年前学运的画面,想起一个学生对我说:“我不要搞政治,也不要参与这些东西”时,我说:“这不是政治,你那么年轻,去旁边感受一下那种激昂吧!”
这么说好了,你的生命有没有什么不切实际的梦想?没错,就是不切实际,因为青春如果太切合实际,就不配叫青春了。
因为青春本来就是一个巨大的梦想的嘉年华。
参加学运的人不一定都是为了政治目的,有些人是为了朋友参加而参加,他们甚至不知道游行议题到底是什么。但是,曾经感受过那份激昂的人一生都不会忘记。
也许我应该再写一篇有关台湾学运的小说,因为世界上很少有学运这么成功。当年参与野百合学运的人,如今都身居要职,这时候对学运的反省和检讨,以及对参与的革命者内在孤独感的检视,会是一个有趣的题目。为什么十年来没有学运了?是社会改革了?还是所有梦想不再有激情了?
03
▼
梦醒时分
七零年代我在巴黎参加安那其组织,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巴黎的一个地下室,办一个叫《欧洲通讯》的刊物。很多人出去工作,赚了钱回来放在一个筒子里,大家一起用。
后来我退出是因为发现有人偷筒子里的钱,那大概是我的梦醒时分了吧!我觉得,如此高贵的团体里怎么会有这么肮脏的事?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革命者的孤独是革命者迷恋自己年轻时的洁癖,并且深信不疑。你相信理想是极其美好的,而且每个人都做得到,你也相信每个人的道德都是高尚的,会愿意共同为了这个理想而努力。
在克鲁泡特金的作品里,一直相信人类终有一天会不需要政府,自动自发地去缴税、去建设,不需要他人来管理。现在的我则相信这个社会一定会有阶级,一定会有穷人与富人。
当你有天说出“哪一个社会没有乞丐?”时,就表示你已经不再年轻了。
然而,只是你已过了梦想的年岁,年轻时候的洁癖仍然会跟着你,在某一刹那中出现,让你寝食难安,让你想问:“是不是已经老了?是不是已经放弃当年的那些梦想?”
如果说年轻时的梦想是百分之百,过了二十五岁以后会开始磨损,也许只剩下百分之八十、五十,或是更少,但是孤独感仍在。即使都不跟别人谈了,仍是内心最深最深的心事。
我的小说《安那其的头发》是将头发的意象和革命者的孤独结合在一起。可能读者对这篇小说所写的领域感到陌生,原因之一在于台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思想是被垄断的,缺乏不同信仰之间的辩论,甚至当年参与学运的领袖都不一定拥有思辨的习惯。学运成功得非常快,大部分的学运领袖变成政府官员,他们没有时间继续保持革命者的孤独,去酝酿对其社会理想进行思辨的习惯。
对于台湾学运发展的过程,一方面我们会庆幸对一个保守到开始腐朽的政府,在最短的时间内引起社会的反省与检讨;可是另一方面,新的力量立刻取代旧的,反而无法延续反省检讨。
04
▼
佛学与革命
清代末年有很多动人的革命者形象,其中之一就是谭嗣同。他是学佛的人,却走向激烈的革命,康梁变法失败时,其实他是可以逃跑的,但他对梁启超说:“你一定要走,我一定要留。没有人走,革命无以成功;没有人留,无以告诉所有曾经相信这次革命的人。”他决定扮演走向刑场的角色。
我相信,谭嗣同内心有一种空幻、虚无、无以名状的孤独,使其将佛学和革命纠结在一起。当他觉得生命是最大的空幻时,他会选择用生命去做一件最激情的事情。
瞿秋白也是一个学佛的文人,会刻印、写书法、搞诗词,但是他突然对文人世界的萎靡感到不耐,决定出走。所以在一九一七年听到俄国发生革命时,进了同文馆苦学俄文,他相信俄国革命成功了,中国革命也一定能成。
后来他成为了共产党的领袖,之后在福建被抓,写下了一本很重要的临终作品——《多余的话》。他在这里边谈到,自己根本不适合作为共产党,更不适合当一名领袖,他无法抛弃内心对唯美的追求。
瞿秋白最后要枪决时,正面对着枪口,唱着自己翻译的《国际歌》结束生命。他留下一首诗:“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同。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一个共产党领袖最后写出来的绝命诗,根本就是一个高僧的句子。
05
▼
如果还有文学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美丽岛事件?当时很多人都卷入了这件事,包括小说家王拓。王拓的父亲和哥哥都是渔民,相继丧生海上,他在小说里写八斗子家族的故事,却在那个年代被套上“鼓吹阶级革命”的罪名受到挞伐。
王拓是当时的受压迫者,为渔民的悲苦发声,使人相信文学应该要涉足生命的领域,但今日的文学,如果还有文学,它的触手应该伸向何方?
前阵子,我在电视新闻中看到两个人,一个是王拓,一个是诗人詹澈,前者代表民进党,后者代表民间的声音。看到这个画面,我有很深的感触,他们都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可是目前他们代表的其实是两种对立的角色。
这个社会当然需要不同的角色,可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两个人的对比立刻反映了角色的荒谬性。
我不在意政党政治,我在意的是在家庭、在学校、在社会、在政治中,那个克鲁泡特金自称的“反叛者”角色,还在不在?
反叛者不会是社会里那个“听话的人”,而是一个让你恨的牙痒痒的人,他扮演的是平衡的角色和力量。有的社会对反叛者是急欲除之而后快,有的社会则是把反叛者视为“你”和“我”互动所形成的推力,我想后者是比前者可爱多了。
“革命”这个词长期以来与“政治”画上等号,但我相信它应该有一个更大的意义,就是如克鲁泡特金所说的“反叛者”,是对自我生活保持一种不满足的状态进而背叛,并维持背叛一个绝对的高度。
我真的觉得革命并不理性,是一种激情。而古今中外的革命者,都是诗人,他们用血泪写诗,他们用生命写诗,他们所留下的不只是文字语言的美好,更多是生命华贵的形式。
我相信,现实的政治其实是梦想的终结者,如果现实的政治能保有一点点梦想,将是非常非常的可贵。
结语:小伙伴们,在今天的共读中我们看到,革命者的孤独是他们迷恋自己年轻时的洁癖,并且深信不疑,他们相信理想是极其美好的,每个人的道德都是高尚的。当不再年轻时,才恍然发现并非如此。蒋勋先生对台湾曾进行的“野百合学会”的结局庆幸又遗憾,不管怎样,他都希望人们对社会理想具有思辨的习惯,并且不断反省与检讨。
明天,我们将开启新的一章“暴力孤独”。让我们期待明天的共读。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可以在文章底部给我们留言点赞。阅读好书,自我成长,相遇十点,读你每天!我们明天见,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