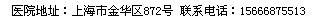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洁癖 > 洁癖症状 > 这篇小说,让我们看到了陕西ldquo
这篇小说,让我们看到了陕西ldquo
北京哪家皮肤病医院好 http://m.39.net/pf/a_6171969.html
书房小说·评论
书房MOOK主持人丨王闷闷向现实的理想主义者致敬
——李曼瑞《拴柱和天龙》读后
宋宁刚
《拴柱和天龙》(发表《中国作家》年第5期)是“95后”陕西青年作家李曼瑞的短篇小说。全文两万余字,一路读来,文字清畅,格调不凡,可圈可点之处颇多,令人格外惊喜。
仅看题目,或许会以为,小说主人公是两个人物。及至读小说正文,很快会明白,其实是一个人:拴柱是主人公的在陕西老家(西安城北一百多公里外的农村)时的名字,天龙则是他到了北京之后自取的名字。拴柱和天龙,一如其名字,意涵着两种不同的生命形态。拴柱是父母给他的名字,正如他的身体也源自父母,是他社会身份的实然,试图把他牢牢拴在一根柱子上;天龙则是他对自己的期望,不甘被拴住——他想成为一飞冲天的龙(即使在逼仄的空间中,宛如池中之龙,无从伸展),意味着现实之上的理想,以及自我灵性生命的觉醒与希求。而小说的叙事,也就在理想与现实的张力中发展。
一
在这篇小说中,青年画家张天龙是个满怀理想的“北漂”。他18岁时,他离开老家去北京参加中央美院的艺考,虽然最后没能成功,却宁可在北京上三流大学,也不愿回西安,冲的就是方便去考中央美院的研究生。在追逐理想的道路上,张天龙是不幸者,也是幸运者。说不幸,因为大学毕业后,他连考13年,因为英语的原因,都没有如愿以偿地考上美院;说幸运,因为他在美院对面的一个售卖画材和书籍的美术书店找到了一份工作,并且干得不错。正因此,他不仅有了一个栖身之地,可以自食其力,而且从实际距离来说,也离美院更近了。最重要的是,十多次考研的挫折,都没有让他失去信心,也没有让他变得愤世和偏执,相反,他的画艺不断长进,他也依然阳光、坚定,不仅心存理想,而且尽力实践着自己的理想。对于一个以艺术为生命追求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幸运?
不过,这幸运并不是所谓上天的赐予,而是他通过大约二十年不懈的努力所挣得的(如果从他中学学画算起,历经大学四年,考研十三年,也有差不多二十年了)。他的坚定,一如他在红房子书店的打工经历,“从那时到现在,红房子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般,几乎两个月都会换一拨央美学生在这里勤工俭学,又大浪淘沙一般退去,到了张天龙却定住了”。正是靠着这种水滴石穿的精神,他不仅能够糊口,还能寄钱给家里;此外,在艺术创作上也大踏步地前进。小说中描写张天龙专注于作画的文字尤其动人:
每天店里关了门,张天龙把床铺上的被褥卷起来,抽出摞在床板上的画板,支靠在对面墙上,就坐在床沿上开始画画。多少年如一日,自律的张天龙不约会、不看电影、不上网、不玩手机,也不和老乡同学喝啤酒、撸串儿、吹牛、谝闲传,他听着音乐,可以一直从傍晚八点店里关门画到半夜十二点。睡前他把画了一半的画板重新搁回床板上,再铺上被褥睡觉。
这种精进的精神和格调,由一个青年作家的笔写来,也格外引人注目。这样的精神、毅力和十数年如一日的努力,何尝不是作者的内心展现,或说自我期许?又何尝不是作者对同样满怀理想的人们的感召?
二
从创作风格及其倾向来说,《拴柱与天龙》是现实主义的。这也是陕西文学目前为止的主流写作方式。但是,李曼瑞的不同之处在于,她笔下的现实主义带有可贵的理想气质。这种气质既显示在张天龙的个性与追求中,也通篇透显在小说的整体氛围中。这种气质也许与作者的年龄有关,但我更愿意将之看作是创作者的精神格调使然。当下的现实主义写作,已经很少见这样带有真诚的理想之美的写作格调了。更常见的,要么是灰暗、迷茫的现实主义,要么是看似具有理想,实则是轻佻和谄媚的现实主义——无论哪种情形,根本上来说都是一样,是目光浑浊、内心混乱,缺乏精神向度的现实主义。
说起来,《拴柱和天龙》的故事骨架,一点都不算新鲜:年关时节,一个“北漂”青年被母亲逼婚无奈,想找个假女友应付;结果,穷小子真的遇到了才女……如此概括起来,几乎有点俗套。实际上,这样的概括是粗暴的、甚至轻率的,因为真正决定文学高下的,并非写什么,而是怎么写。否则,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小镇、福克纳笔下邮票大小的地方,何以会成就他们成为伟大的作家?
质言之,如果忽略了小说中非常宝贵的细节来谈小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这一点,对《拴柱与天龙》来说,也不例外。正是因为作者绵密的叙事所构成的皮肤和筋肉,故事的骨架才不显得生硬、突兀和俗套。这是作者出色的创作能力的体现,也是这篇小说最可称道的地方之一。
同样,这也是《拴柱和天龙》虽然同为现实主义,但是与当前的许多现实主义写法,非常不同的地方。常见的现实主义,不仅小说叙事的总体走向不大会出人意料,而且具体的叙述也不大能叫人信服。而《拴柱和天龙》的叙事,虽然基本走向我们能够猜到,但是其叙述本身很好地支持了这种走向,不会令读者觉得勉强。实际上,小说虽然整体基调是现实主义的,但在很多地方都超出了现实主义,比如拴柱和天龙的人名设置,比如特意将主人公的卧室简画室安置在3.14平方米的空间中(这个数字同样意味深长,虽然实际空间窄小,但作为圆周率的数字,它似乎暗示着某种值得期待的完成和圆满)。而在小说最后一节,通过主人公的梦,将现实主义的写法高度象征化,以作为全篇之结束,更是堪称精彩、高妙。如此别有匠心的安置,在同类型的写作中,即使不是极为罕见的,也是极为难得的。
同样颇有意味的是,虽然小说的写法是理想的现实主义,其小说主人公的精神质地,却是现实的理想主义,也即是可能的、而非凌空虚蹈的现实主义。
三
作为一篇以现实主义手法为主的小说,《拴柱与天龙》特别令人激赏的地方还在于,作者对自己所写的对象及其相关领域之问题的熟稔,有些地方还有不凡的见解。
比如,小说中写怀揣着画家梦的书店店员的张天龙,在书店里一边打工一边临摹《富春山居图》:
他没有多喜欢黄公望,可这个《富春山居图》也至少临摹了三四遍,眼下这册页的纸质很不错,在扁长的空白里画一个微缩版的铅笔小画很有感觉。张天龙饶有兴致地换了一支2B铅笔,开始在山峦上画小小的树,渐渐的,一片山水便形成了,很苍茫。他画得认真,就忘了他要面对的麻烦,只沉浸在这简单的享受里。
“渐渐的,一片山水便形成了,很茫茫”!“苍茫”二字用得多好!没有对艺术相当的感觉和认识,这两个字是呈现不出的。当然,没有对艺术的沉浸,更写不出张天龙画画时那种“简单的享受”式的沉浸。这种书写,既是一个作家写作相关题材时必备的功夫,也是一个作家的暗功夫。然而这一点,很多写作者都做不到,或者说,很难充分地做到。
处于小说核心位置的两节(第三节和第四节)内容,尤其能够体现主人公的艺术功底,也可见他的艺术理想不是凭空而来的。同样,它们也深入地反映了作者的专业素养。
小说写张天龙帮助一对母女买颜料:
张天龙把她们选好的四盒颜料拿上,领着她俩往水彩颜料柜台边走边说,大姐,市面上流行的水彩颜料有国产马力、国产鲁本斯、樱花、温莎牛顿、吉祥颜彩、凤凰颜彩、美丽蓝蜂鸟、荷尔拜因、史明克、MG,我说的基本是从低档到高档的顺序,各有各的受众人群……
当那个母亲表示,自己可能买多了的时候——
张天龙不置可否地说,关键是您选的都是高档级别的艺术家专用,初学的学生大多从国产马力、日本樱花、国产温莎牛顿开始,您要嫌太次,那就直接用中档次的荷兰梵高和伦勃朗、英国歌文、国产鲁本斯、俄罗斯白夜,大部分在两三百块钱。像您选的德国史明克、MG艺术家级的管彩,是顶级的了,学生初学用太可惜了。而且她不是专业画画,打开了画几个月再放几个月,时间一长就不好用了。
最后,张天龙建议小女孩选择固体彩色颜料,从画小画开始:
你是新手,刚开始画比较重要的是学会饱和度和透明度,你还得学会用混色。以后你慢慢学着把握颜色的扩散和水痕,就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牌子的颜色了。不同牌子的水彩有不同的特点,比方说美丽蓝蜂鸟,特点是扩散性非常好,而且颜色亮丽清透!它的暖色系和蓝色系真是很漂亮;MG有几款很有名的矿物色,是宝石直接磨成粉,和国画的矿物质颜料一样,土豪级别!画出来的效果颜色很变幻,会沉淀,新手一定控制不好的,那就别要;还有你妈帮你选的史明克,传说中的高级灰,德国人的颜色特别沉稳特别淡雅!但它不适合你,那是画传统写实风的艺术家用的,你也别买了。
这样高度专业的解说,既令读者耳目一新,又因为将其置于具体的小说情境中而不叫人觉得枯燥,读来只令人觉得精彩。
更精彩的,则是紧随其后,张天龙与买书的顾客关于吴昌硕与齐白石的艺术差异及其高下的争论。这段争论几乎会令人想起《红楼梦》中“香菱学诗”一节。即使我们对小说中张天龙所说的观点,有所疑问、有所保留,也很难简单地否定他。这样的艺术见解所体现的,不仅是主人公的专业眼光,也是一个深入艺术的创作者的眼光,更是作者内在极为专业的艺术素养的呈现(李曼瑞自己就是中央美院史论专业毕业的,谈起这些,自然是她的当家本领)。
四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无论多好的情节和思想,都需要文字来传达。一个现实则是,当下很多作家的文字或随意,或粗率,即使有些名作家的文字,读来都叫人大失其望。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在批评这种现象时说:
中国文学批评也喜欢“寻章摘句”,也喜欢“批文入情”,所谓“寻枝振叶,沿波讨源”,强调从字里行间悟入,文本分析的传统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一直都很自觉。别的不说,古人在语言文字上几乎都有洁癖,像今天许多批评界同行捂着鼻子,对许多语文基本功都没过关的恶劣文本分析来分析去,力图越过语言文字,发觉背后的微言大义,这在古人看来,也许是不可思议的恶趣味吧。(郜元宝:《“作家论”的转变与重建》,《中华读书报》年1月11日)
说郜元宝所指出的这种“恶趣味”,在当下的文学创作、尤其小说创作中俯拾即是,并不夸张。
作家张炜,对此一问题也是痛心疾首。他坦言,批评家“对语言上的不挑剔,究其实是道业上的平庸,再言重一点就是品格上的堕落。能够察省至此并谈得透彻需要锐勇……这种不挑剔也是向时风强势的一种迁就或依附。因为粗蛮的力量总是人世间最强大的一股力量。”而一个写作者,“如果在文字上突兀地慌促起来,以至于到了杂乱无章目不忍睹的地步,不仅是不足观,而一定在透露出其他信息:急遽地投向势利,这几乎无一例外。”(张炜:《人固有心曲——读郜元宝“三议”》,《当代作家评论》年第2期)
与许多作家对文字的不讲究、不认真相反,《拴柱与天龙》的文字清明、畅达,读来不仅令人愉快,而且振奋,充满期待。
某种程度上说,这篇小说,无论是其理想气质的格调,还是带有诗性艺术判断力的人物对话,如果没有通过作者清隽、畅达的文字体现出来,都是要大打折扣的。就此来说,《拴柱与天龙》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95”后青年作家的写作才能和精神格调,更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值得信赖和期待的写作态度,一种令人振奋和惊喜的生命态度。虽然作者表示,“现实中,小说《拴柱和天龙》中的拴柱张天龙、林亦诗、红房子画具书店、3.14平米的睡房兼画室,甚至连同中央美术学院都不是真实存在的”,并说自己所“描写的不过是每一个追梦的、热爱艺术的人们,每一个尚在苦苦坚持的苦涩现实,和每一个华丽的理想而已”,但是,它们未必不会成为现实,现实中也未必没有像张天龙这样满怀“华丽的理想”追梦者。就此来说,我更愿意将之视为一种不甘平庸的生命的永恒追求。
作家肖像
李曼瑞,作家。年出生于陕西西安,本科于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十六岁获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十七岁获全国创新作文大赛一等奖,并出版长篇小说《十七岁的围城》,正在被改编为电影。文学作品发表于《中国作家》、《北京文学》、《青年文学》。
书房MOOK批评者丨宋宁刚
宋宁刚,80后,诗人、学者。南京大学哲学博士。出版有诗集《你的光:-》(上海,)、《小远与阿巴斯》,(北京,)、《写给孩子的诗》(西安,),诗论集《沙与世界:二十首现代诗的细读》(北京,)、《长安诗心:新世纪陕西诗歌散论》(北京,),随笔集《语言与思想之间》(西安,)、《纸上的关怀》(上海,),译著《怪作家》(桂林,)等。现为西安财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延伸阅读
李曼瑞:拴柱和天龙丨书房MOOK
~近期好书好物推荐~
▼▼▼
▼点击阅读原文,颠覆你对历史的认知。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