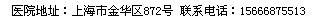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洁癖 > 洁癖症状 > 原创日本民族性格的名声情结
原创日本民族性格的名声情结
日本民族性格的名声情结
提及日本,首先想到的是“菊与刀”。日本的民族性格是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的,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的,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的。他们十分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而当别人对他们的劣迹毫无所知时,他们又会被自己的罪恶感所击倒。他们的士兵规规矩矩,但骨子里却又生性叛逆。如此对立的两个事物如何会统一于日本人身上,其根源之一在于“名声”。
“名声”分两种,“荣誉”与“耻辱”。“荣誉”是日本人毕生之追求。“荣誉”分为两种,一种是大至国家的“效忠”,另一种是微至日常的“素养”。日本人的“荣誉感”极强,是不可玷污的,他们几乎是有精神洁癖的。日本人极其追求清洁,不论是生活还是精神。精神层面追求清高,君子之交,追求忠诚,贞洁。爱清洁已然成为他们的一种洁癖,正如,冈仓由三郎所说:“日本人喜欢干净,没有污秽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平静而美丽,犹如一枝盛开的樱花。”正式对这种清洁的追求,日本人重名声,重修养。为了避免非议,他们苛刻的要求自己,洁身自好。将自己活成了一株菊,淡雅风骨颇有“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的气度,然而,如果自身的名声被玷污,那么,就要涉及到“耻辱”。
正是基于日本人的精神洁癖,因此不允许任何人玷污他们的名声。在前明治时期,日本人对待嘲弄自己,玷污自己名声的人,不论是宗主还是其他人,他们的选择一律是“报复”。纵观那些描写日本的历史故事,皆可反映这个鲜明的主题,受辱一方会报复施辱一方,为受辱而复仇,哪怕施辱者是身存依附的宗主。即使是被誉为日本最善良的人物之一的新户渡导造也认为:“在复仇中存在着某种能满足人的正义感的东西。复仇意识有时像数学题一样精确,在方程式的两边求得相等之前,我们会一直认为这道题没有做完。’在一本《日本的生活与思想》中冈仓由三郎把复仇和一种特别具有日本特征的风俗做了类比,他将精神受辱和身上的污秽,创口做类比。那么多污秽与创口,如果不通过申辩的彻底清洗,是不可能变得干净且痊愈的,而复仇正是在完成这一工作,复仇就像是日本人的晨浴,洗掉别人仍到你身上的泥垢,只要有一丁点的泥垢粘在你身上,你就不可能是贞洁的。虽然,在大多数国家的伦理教条中,除非一个人自己认为受到了侮辱,否则就不能受辱,受辱来自内心而非针对自己的言行。遗憾的是,日本没有这种伦理,这使得日本人极易受辱,毕竟你不能保障每个人都认同赞赏你,这也使得极其自重的日本人易走极端,性格暴戾。日本的传统中一直在公众面前保留着这种“晨浴”般的复仇理想。在当时,由于法律控制力尚未成型,报复的形式更倾向于直接的暴力性攻击,以刺杀仇人为荣耀。如今,在现行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现代文明的约束下,日本人虽然依旧执念于“名声”捍卫战,但是,形式上已经从过去直接的积极性进攻转向了消极性的保守防卫。计谋报复,内心仇视成了更为主流的选项。暴戾,放肆,惨无人性的刀文化也应运而生。刀文化最初是日本人捍卫名声的工具。
就像机体免疫过激原理,原始心理的名声捍卫除了强烈的攻击性,还奇妙的存在强烈的排己性。日本人极易因为失败,受辱和被排斥而受挫,一蹶不振。一旦遇到挫折,外部矛盾从具体变得抽象,他们大多选择折磨自己而不是迁怒他人。所以,在大多数小说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修养层级较高的日本人一会犹豫的要死,一会又愤怒的要命,常常为此迷失自己,厌烦一切,厌烦自己,厌烦家人,厌烦世界。这种厌烦不仅是因为理想与现实的对立,也不仅是求而不得的失意,是一种自我式的绝望到了骨子里的孤独,是一个敏感型民族太容易受伤的病态表现,他们害怕被拒绝,并把这种恐惧引向内心,成为碍手碍脚的东西,他们极易阴郁,并将这种阴郁安置在内心深处,他们的阴郁没有由头,他们可能会抓住某个小事作为由头,阴郁的象征而已,他们敏感脆弱到了极致。而这一切的结果多是使文化性格内倾的日本人一次次强化自己的内心指向,更加抑郁倦怠。现如今,自杀就是现代日本人对自己采取的最极端的攻击行为的鲜明表现。相较于古代日本战场没有生还希望而选择自杀来有尊严的结束生命,现代日本人的自杀更倾向于一种放弃生选择去死的方式,更倾向于日本民族性格中为了所强调的贞洁而自取灭亡,有种幻灭的美感。极端又纯粹。
同时,日本人也利用这种免疫体质的内心指向性,宣扬狭隘的民族主义,将攻击的矛头从自己的胸口调转,进而攻击其他民族,在针对外国的极权主义侵略中,他们重新“找到自我”,因此,从这一点上说,日本民族发动战争的源头来自于强排异的脆弱内心。所以,日本人的自重,自豪,甚至于自大,日本人看似忠诚又极端自洁自负等等矛盾现象似乎都有了答案,那就是日本人的精神特性,源于对纯洁的爱和与之互补的对污秽的恨。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中日关系复杂敏感的今天,了解日本,尤其日本民族的民族性格才是大国博弈的重要一着。
赞赏